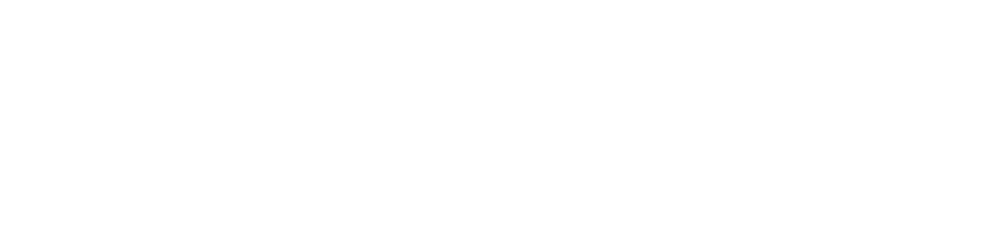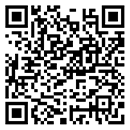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李汉俊的研究似乎缺乏足够的重视,据统计近20多年来有关李汉俊的介绍及研究文章仅有三十余篇。(1)而且研究的面也比较窄,主要集中在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建党的贡献以及李汉俊脱党原因的探讨等方面。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深入透彻的程度,对李汉俊思想的研究更近似空白。这种情况我认为是跟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值此李汉俊烈士牺牲80周年之际,我想对建党时期李汉俊的思想进行一番初步梳理和探究,以便我们对李汉俊在建党时期的地位能够做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此作为对革命烈士的一种纪念。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李汉俊在建党时期的思想作一简要论述。
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五四以后,面对中国积贫积弱和军阀政府黑暗统治的社会现实,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所有进步的中国人都在思考怎样改造中国这个问题。而当时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什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互助运动、新村运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各式各样的方法和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扰扰,使人如坠云雾,一时摸不着方向。与此相反,李汉俊却很早就辨清了方向,那就是中国必须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在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这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以后,工业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也越发明显的时候。随着从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在日本开始成立。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流派中,马克思主义亦成为一些日本社会主义者研究和传播的对象。身在日本的李汉俊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结识了一些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进步人士如界利彦、宫崎滔天等。李汉俊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样,经过反复推求和比较,终于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李汉俊盛赞马克思学说是现在理论的最高成就,对后进的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2)
1919年8月,回国不久的李汉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著的《世界思潮之方向》,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连载,文章热情讴歌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指出:“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形势日日变化。”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已成为世界潮流之方向。“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飞猛进。已经成了一大势。”在文章的结尾李汉俊自问自答说:“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3)
随后李汉俊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佐野学的《劳动者运动之指导伦理》时,更称社会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形成相伴而生的以图解决劳工问题的一类思想。是一种主张建立完全消灭劳力榨取制度的“新文明”。(4)
李汉俊之所以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一方面是因为李汉俊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研究(他曾先后翻译过《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价值、价格与利润》、《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序言等),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世界近代历史和中国的社会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李汉俊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近代文明和罪恶的根源”,它独占生产资料,垄断市场。李汉俊称资本家是强盗,资产阶级是强盗阶级,因为他们“以国家、法律、道德为堡垒、以智识为武器、以金钱为弹丸、在青天白日之下、万目环视之中、掠夺平民财产、剥削平民血汗。”他说资本家与一般强盗的区别“不过一个是用制度的势力去抢、一个是用破坏制度的个人腕力去抢罢了。所以说资本家是强盗、资本家阶级是强盗阶级。”(5)李汉俊进一步说:“我们虽然没有因资本主义下的产业发展,像先进各国人民受过那样苦痛;但因先进各国人民的教训,也就应该晓得非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产业了。” (6)
所以资本主义虽然使生产工具有了极大的发展,生产力有了高速度的进步,但是它终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李汉俊在《中国的乱源及其归宿》一文中说道:“俄国的社会革命,决不是一俄国人底事,也决不只是一俄国底事,也决不表示发生社会革命的环境只在俄国成就了;乃是全世界人都要推翻资本主义的表现。……总之资本主义底崩坏在世界已经是一定的必然了。”(7)
李汉俊认为中国如要赶上世界进步的步伐,就只有走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他在《我们如何使中国的混乱赶快终止?》一文中说道:“中国的混乱是中国进化急速的表现,要到进化到了社会主义,才能终止。我们要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自然要努力使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 同时李汉俊还说道:“现在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没有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的必要,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上走去,并且资本主义在现在的中国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以中国现在的环境又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路上走去的必要。”(8)
李汉俊说:“中国底生产力虽然没有发达到能够使中国人发生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意志,但因先进各国底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充分发展的产业底下受了痛苦的教训,中国人就可以发生这意志了。”(9)
李汉俊主张的社会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俄式的社会主义。为了实现他的主张他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对于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李汉俊均做了介绍,并总结出社会主义的最低限度的基本原理为:“在一般社会上取平均主义,在产业上使产业机关为社会共有,使分配平等。”通过比较,他认识到近世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底社会主义为中枢”。(10)
期间李汉俊翻译和撰写了许多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如《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新青年》8卷1号)、《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新青年》8卷1号)、《苏维埃共和国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新青年》8卷2号)、《劳农制度研究》(《共产党》第5号)等,在他看来,中国要真正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就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苏俄式的劳农政权。
李汉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各国都是不一样的,在法国为工团主义,在英国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德国为社会民主党,在美国为I.W.W,在俄国为布尔什维克,……其实除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无相同之处。”(11)
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李汉俊对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驳,针对张东荪所说的:“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既不像工行的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全国工行,又不像多数的社会主义组织一个无产者专政政治,更不像无治的社会主义废去一切机关,复不像国家的社会主义把所有生产收归国有,乃是浑朴的趋向。”李汉俊尖锐地质问:“既然是主义,一定有一个内容;断没有只有趋向而无内容的,可以说是主义。”同时李汉俊说明:“社会主义、虽然也有人说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但这不过是因其内容复杂、不能像别的主义、下严格的定义罢了、不是说他无内容的。”“决不只是一个趋向。唯有东荪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无内容的、仅有一个趋向、并且还是一个浑朴的趋向。” 他的那个社会主义“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社会主义,“是他一个人的社会主义”。(12)
李汉俊在《社会主义是教人穷的吗?》一文中,批驳了张东荪“要使他们能够营‘人的生活’”“就想到要发展实业,因为要发展实业就要主张资本主义。因为要发展资本主义,于是就反对社会主义。”(13)揭露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实面目。
从一些同时代人的回忆来看李汉俊确实是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董必武曾经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4)日本记者芥川龙之介也说:“李氏年方28,从信仰上看,他是个社会主义者。”(15)
二、反对改良和调和;主张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
有人说李汉俊有改良思想,(16)李汉俊不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7)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认为恰恰相反,李汉俊是反对改良和调和的,他是主张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
早在1919年10月,李汉俊在写给董必武的一封1.5万字的长信中,就详细地阐述了他对于社会改造的意见,李汉俊在信中对调和主义和教育救国论这两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调和主义是英国政治家用的一个词,调和是用在性质相同,不过质量有点轻重,颜色有点浓淡的东西里面的,中国与英国的历史背景、价值观、社会性质均不同,而中国的调和者,看不到这些,用英国进化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通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说明中国不能实行调和主义,只能革命。教育与社会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李汉俊说:“我向来不信局部的改良,不信有局部的改良,不信局部能够单独改良。”“要改造局部,就非破坏了那个全部,另造出一个适合这个局部的有机的全部。”“没有旧的破坏就没有新的建设。没有旧的全部破坏,断没有新的全部改造。断没有新的局部的改良。这个旧的与新的、旧的全部与新的局部,新的全部与旧的局部,是没有调和的。”“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18)
1920年4月,李汉俊对来访的日本《大阪每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芥川龙之介、记者村田孜郎两人说:“当今中国该走什么路?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共和也非复辟,这般的政治变革是改造不了中国的。过去既已证明了这点,现在亦证明了这点。那么,我们该努力去做的唯有社会革命一条路。” (19)
当时调和主义一度盛行,李汉俊积极揭露它的欺骗实质,他提醒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立阶级,阶级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劳动者只有对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才有出路。
李汉俊在《调和者与神经病》一文中,讽刺抱定“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并非劳动运动的唯一手段”的美国劳工联盟主席龚伯斯,说他试图调和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准备在华盛顿召开的“劳资协议会”上通过国际劳动者保护条例,又适逢I.W.W运动,两面夹击下,竟得了精神病。(20)
1920年春,日本出版了一本叫《三益主义》的书,说是照它那个法子,可以做到资本家也得益、劳动者也得益、消费者也得益的地步,可以免除阶级的斗争,作成阶级的互助,李汉俊说这真是要让人笑弯了腰。“互助上面加上阶级两个字、天下有这么好的互助方法、恐怕太阳要从西边出来呢?”(21)
李汉俊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希望“工人对于工人讲互助。而不希望工人对于资本家相冲突。”的调和主义观点也进行了批驳。李汉俊指出:“近代产业底发生、其必然的结果、一定产生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底对立。”工人“他们底相互间的同情心、互助观念、团结、组织;一定是要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晓得他们的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他们底利害是一致;晓得他们底利益不是巴结资本家、互相排挤敌视、可以得到、一定是要以资本家为敌标、互相援助、才可以得到;才能发生、才能成立的。”“而张东荪君只希望工人对于工人发生同情心、工人对于同阶级发生互助观念、工人有团结有组织;而不希望工人有阶级觉悟;这是叫人走投无路么?”(22)
李汉俊十分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在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民主主义,而阶级斗争学说犹如一条金线将这三大部分从根本上缝起来,使“其为一个完整的大的组成部分。”(23)李汉俊还认为:“社会组织底变革是要人底意志底——或为其表现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离开了阶级斗争来解释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就要变为机械论。”(24)阶级斗争的手段有许多种,最有效的手段是像俄国那样,用暴力彻底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
同时李汉俊对什么叫革命进行了介绍,他说:“革命呢?是要将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一切旧来的思想、道德、制度、组织、从根本上推翻完全、在新基础上。改建社会的运动。这种革命是鼓动知识阶级的新思想,和从实际的经济的压迫、不得不起的、贫民阶级的反抗运动、两种激流相合时所激发的。”(25)
1921年6月7日,李汉俊在《共产党》月刊第5期发表了《劳农制度研究》,对俄国的社会主义劳农制度进行了热情的宣扬和介绍。第一次较为详尽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苏俄政治制度的产生、结构、运作等。他指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实现了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这种政治制度是“根据阶级对立的事实,以产业的单位所举的代表做基础的。”在俄国革命中,具体产生了劳农会(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劳农会。”李汉俊在《劳农制度研究》一文中,还阐述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中间,有一个革命的过渡期。这个就叫做政治上的过渡期。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
三、反对加入国民党;主张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李汉俊与《星期评论》社的同事戴季陶、沈玄庐等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为什么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待革命的实践上,戴季陶、沈玄庐等仅仅限于宣传,一遇到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时候,便退出了“联合战线”。而李汉俊却勇往直前,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来。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初成果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李汉俊是这个伟大成果的直接参加者和组织者。
过去有人说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不赞成组织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26)我认为事实也并非如此。
事实上,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一篇名为《世界思潮之方向》的译文中说:“译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说,……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说明他已经有了加入政党的想法。据此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民党”指的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因此李汉俊是最早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人。(27)也有学者认为李汉俊所说的“民党”,并非指共产党,而是国民党。(28)我同意后一种观点。仔细研读李汉俊文章后我们可以知道,李汉俊文中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当时有人叫李汉俊加入国民党,但是李汉俊并不想加入国民党,因为在他看来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有希望的党,它的现状令人失望,他想要加入的是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时中国还没有那样的党。中国革命的情形命他不能去做民党、革命党。因为那里只有“政治、权利、联合、妥协”。而李汉俊“只是平民、民众、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李汉俊自问“我要个什么。我去取个什么?要谁给呢?管他给不给呢?”很明显李汉俊要的是社会主义,是向资产阶级去要,不管他给不给,都要去要的。(29)
以后的事实证明就是如此,1920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会议上,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坚决赞成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正式成立。李汉俊是八个发起人之一。李汉俊还为新成立的共产党起草了一个类似党纲的文件。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中说:“一九二0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的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这样,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30)
张国焘回忆说:“陈先生(陈独秀)向我表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一致表示赞成。” (31)包惠僧也说:“当时上海方面的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和北京方面的李大钊,一致主张成立中国共产党”。(32)
此外李汉俊还负责帮助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联络工作。1920年夏,他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希望武汉也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33)
四、反对空谈,主张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
也有人说李汉俊不主张立即进行职工会的组织、而要集中力量做学生运动与宣传工作,(34)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35)这也同样不是事实。
事实上李汉俊是反对空谈,主张从事实际工作的。1919年9月,他在《时局怎么样?》一文中说道:“希望解放和改造的国民啊!解放和改造,是要从‘努力’和‘奋斗’当中去求,‘冥想’是不中用的。‘依附’是不中用的。‘雷同’是不中用的,拿出不妥协不退让的精神来。去作‘孤立的奋斗’,拿出‘创造的真精神’来,去作大破坏,大建设的工夫,中国人的生命,才有复活的日子。”(36)
同时李汉俊积极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与工人相结合,他认为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李汉俊在解释什么叫革命时说:“革命呢?是要将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一切旧来的思想、道德、制度、组织、从根本上推翻完全、在新基础上。改建社会的运动。这种革命是鼓动知识阶级的新思想,和从实际的经济的压迫、不得不起的、贫民阶级的反抗运动、两种激流相合时所激发的。”(37)
不久李汉俊又在《上海最近的罢工风潮》一文中提出:“我尤其希望靠‘脑力的劳动’生活的人,应该大家觉悟到我们的地位和永久的利害,是与‘体力的劳动者’一样的。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的开发做工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38)
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20年春,他在与陈独秀等筹建党组织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工人运动。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他和陈独秀等莅会祝贺。他还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帮助他们办工人学校,对工人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作。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在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开发起大会。莅会80余人,大会有上海共产党组织成员李中主持,李汉俊和陈独秀等“惠然来会”,并被聘为名誉会员(39)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这是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李汉俊再次到会给予支持。
1921年2月,上海法租界的电车工人因物价日高,所得工资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团结起来要求增加工资,遭到拒绝,遂决定于28日举行罢工。公司只好答应增加3%,但是过了几天又将这个许愿取消。工人大愤,于3月3日举行了大罢工,经过3天多的斗争,迫使资本家作了让步,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
李汉俊立即在报纸上发表了《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和《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两篇文章。他向读者介绍了罢工的原因、经过,以及斗争的结果,热情地讴歌了电车工人的斗争精神。同年12月7日,汉口六七千人力车夫举行大游行,反对资本家提高租金,经过斗争,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条件。1922年1月3日,李汉俊发表了《汉口人力车夫罢工底教训》一文。他希望工人不仅应该觉悟到要得到生产关系上的“支配权”,而且要得到政治上的“支配权”。
李汉俊离开上海回到武汉工作后,仍然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的火热斗争中去。同时鼓励青年学生号召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去,与工人相结合。1922年5月,他应武汉学联之邀请在汉口举行的国际劳动纪念会上演讲劳工运动史,鼓励学生投身无产阶级运动。1923年初,他对武昌高师社会学系学生说:“我们讲社会问题,光讲些理论知识,若不与实际相结合,体会是不会深刻的。”(40)他曾对一个叫刘弄潮的学生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光从这些经典著作里寻找,主要是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做到言行一致。”(41)为此,1923年1月30日晚,李汉俊不顾危险带领武昌高师历史社会学系学生任开国等四人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李汉俊并不是一个崇尚空谈的“学院派”,而是一个积极的革命实践者。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建党时期李汉俊的思想无疑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潮流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认识的实际状况的,因为首先李汉俊提出了中国社会正确的发展方向,那就是走俄式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李汉俊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手段是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同时李汉俊还提出了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方法是知识分子必须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等一整套完整的社会改造思想。
李汉俊的思想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甚至超前的,譬如李汉俊在当时便已清醒地认识到,实行社会主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他曾经说:“现在人之所以提倡社会主义,未必尽是立刻就想实现。如果说你只提倡而不实行是不配讲社会主义的、这是不行的。如果他一说就能实行了,那里有说的必要呢?”(42)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李汉俊的思想中也存在某些不足和消极的因素。譬如他在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因对某些问题看法不同,而产生矛盾以后。便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失去了信心。他在《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的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对于张闻天先生关于组织党的四个必要条件,及对于党底活动所提意见,表示赞成的同时,转而又说:“我觉得中国人有五个大毛病不容易组织强有力的团体。中国要组织强有力的团体,非首先把这五大毛病除去不行。所谓五大毛病:第一就是猜疑心太深,第二就是责任心太薄,第三就是界限不清,第四就是公私混淆,第五就是责任不明。”(43)
总而言之,我认为从建党时期从李汉俊的思想来看,李汉俊应该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完整的构想,不朝三暮四,人云亦云,即使在离开党的组织以后,仍然在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从事工人运动。以后加在他身上的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中国的经济派、少数派。”(44)等称谓都是不正确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有点上纲上线的味道。
注 释:
(1)《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1949-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1922年6月6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3)1919年9月5日至7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4)1919年9月9日至14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5)汉俊:《强盗阶级底成立》,1920年5月1日《星期评论48号。
(6)汉俊:《我们任何使中国的混乱赶快终止?》,1922年1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7)(8)1922年1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9)汉俊:《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乱源及其解决’》,1922年2月2日至5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10)汉俊:《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1920年5月30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11)《“一大”前后》,<二>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汉俊:《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1920年5月16日《星期评论》第50号。
(13)1921年5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1号。
(14)《“一大”前后》,<二>第371页。
(15)芥川龙之介著《中国游记》,转引《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6)《“一大”前后》,<二>第177页。
(17)《“一大”前后》,<二>第286页。
(18)李人杰:《改造要全部改造》,《建设》第一卷第6号。
(19)同(15)。
(20)1919年10月26日,《星期评论》第21号。
(21)先进:《三益主义》,1920年3月14日《星期评论》。
(22)同(12)。
(23)同(2)。
(24)同(6)。
(25)《世界思潮之方向》,1919年9月5日至7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26)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一大”前后》<二>第286页;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三>第167页。
(27)田子渝:《我国最早提出建党思想的是李汉俊》,1990年9月12日《光明日报》;田子渝著《李汉俊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8)叶累:《最早提出建党思想的是李汉俊吗?》,1999年《上海党史研究》第4期。
(29)1919年9月5日至7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30)《“一大”前后》,<三>第156页。
(31)《“一大”前后》,<二>第138页。
(32)《一大回忆录》第24-33页,知识出版社1980年出版。
(33)《一大回忆录》第3页;《“一大”前后》,<二>第292页。
(34)同(17)。
(35)《“一大”前后》,<三>第137页。
(36)1919年9月21日,《星期评论》第16号。
(37同(25)。
(38)1919年10月26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39)1920年10月6日《民国日报》。
(40)赵春珊《“二七”忆往》。
(41)1981年7月31日,访问刘弄潮记录,转引田子渝著《李汉俊》第119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42)同(12)。
(43)1922年2月6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44)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三>,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