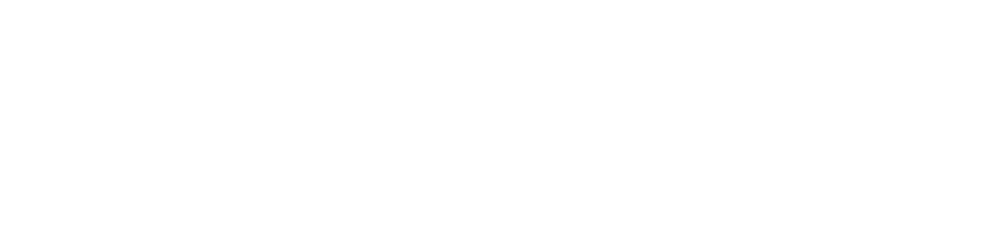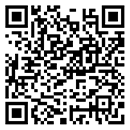张玉菡 姚金果
原载于《北京党史》2016年04期,注释从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党史研究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中共创建史研究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篇,经过学术界不懈的努力,在资料挖掘、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本文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历程、代表性成果、代表性观点等做一梳理,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一、研究概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创建史研究,始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主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一卷(李新、陈铁健主编)的编写工作,后来这本书取名《伟大的开端》。这本书出版前后,研究人员收集、访问的大量资料也被整理出版,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的3册《“一大”前后》。
史料是开展历史研究工作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党史资料的征集、挖掘、整理、编纂和出版工作。除《“一大”前后》外,80年代挖掘、整理、编纂的史料集还有:知识出版社编《一大回忆录》;张国焘回忆录《我的回忆》3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达林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陈公博著、韦慕庭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包惠僧著《包惠僧回忆录》;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孙武霞等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第一辑(1919—1924);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等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等。同时,一些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还编印了一批内部资料集,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重庆市历史学会1979年编《历史资料选编·中国共产党“一大”史料专辑》、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资料室1979年编《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西安师专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和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1979年编《中共“一大”资料汇编》、中央音乐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组1979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等。这一时期,研究刚刚起步,成果不多,除《伟大的开端》外,有张静如等著《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庄有为等编著《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0世纪90年代初,适逢建党70周年,经过十年多的学术积累,国内出版了一批中共创建史专著,如黄峥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马连儒著《中国共产党创始录》、周尚文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史》、张洪祥等主编《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建党75周年时,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问世。郑惠、张静如主编的《中共一大代表丛书》,首次为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国内代表撰写了专题性传记。
1997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出版,开启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一个新阶段。该书是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有关中国革命档案的一部分,共收录205份档案文件,其中98%为首次公布,主要包括1920年至1925年间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契切林、加拉罕、越飞、维经斯基(又译为魏金斯基,化名吴廷康)、鲍罗廷、孙中山、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文电,以及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这些文件都是珍贵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后许多新观点新见解都得益于这批档案资料。
21世纪以来,建党80周年、建党90周年的纪念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发展。建党80周年前后,在史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美)舒衡哲编《张申府访谈录》;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创建的文件共9件,王来棣采访编辑的《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公布了作者于20世纪50年代采访的26位中共早期人物的重要记录。研究方面的著作有:黄修荣著《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曹仲彬著《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刘宋斌、姚金果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马连儒著《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另有倪兴祥编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和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1949.10—2004.12)》,是中共创建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工具书。李良明、钟德涛主编《恽代英年谱》,是恽代英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徐方平著《蔡和森与〈向导〉周报》,探讨了蔡和森如何以《向导》为阵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努力。刘沂生著《魏嵋传》,详细介绍了魏嵋一家在建党初期为党作出的贡献。尽管该书还缺乏原始的文字材料,但其观点有利于推动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和探索山东建党初期的情况。
建党90周年前后,又有一批史料、研究论著出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收录了中共一大13位代表在1917年十月革命至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后所撰写的各种文稿,约150万字,其中,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的文稿都是首次辑录出版,为研究中共一大代表建党时期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张玉菡、李丹阳、田子渝主编《李汉俊文集》收录李汉俊著述、译作142篇,约100万字,是研究李汉俊不可多得的基础性史料。研究著作主要有:邵维正主编《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张军锋著《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齐卫平和张玉菡等合作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苏智良主编《中共建党与上海社会》、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图史》等。苏若群主编《亲历建党》是建党亲历者回忆录的汇编。张珊珍主编《建党伟业》、武国友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前前后后》,是近于通俗性的读物。
为迎接建党95周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推出《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约40万字,披露了1920年至1923年间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关系的专题档案资料,其中许多档案为首次编译出版。该书还收录了157幅档案文件、人物、珍贵书籍的图片,可以通过图片一观档案原貌。
30多年来,国内还有一批中共创建史方面的研究文集陆续出版,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0—2002)》《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论文集(2002—2012)》《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早期组织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汇编了1978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有关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共一大研究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另外,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纪念建党70周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1—14辑),也刊布了许多关于中共创建史方面很有价值的资料,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共创建史的论文。
30多年来,国外学者也比较重视发掘中共创建时期档案史料,并发表、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著。日本学者发扬实证传统,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如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对中共创建史进行了详实的微观考证和研究。以美国、韩国为代表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中共创建史研究也有建树,如A.Dirlik的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Michael Y.L.Luk的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An Ideology in the Making,1920—1928,Hans J.van de Ven的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韩国学者金秀英的博士论文The Comintern and the Far Eastern Communist Movement in Shang hai,1919—1922:The Meaning of Internationalism,S.A.Smith的A Road is Made:Communism in Shanghai,1920—1927,Alxander Panstov的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9—1927,徐相文著《普罗米修斯的天火———革命俄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17—1923)》、2016年出版的尹琳娜·索特尼科娃著《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作的机构》,等等,利用俄罗斯、美国等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如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法、计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口述研究法等深化研究,使中共创建史研究与国际史学发展相接轨,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
另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时期)》,梁怡、李向前主编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介绍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共创建的诸多成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一集) 收录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共创建的论文。
二、专题研究
(一)关于中共创建史时限的界定
关于中共创建史的上限,主流观点有1919年五四运动和1917年十月革命两种。关于下限,则有以下不同观点:一是以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为代表,将下限确定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1919—1923)》、倪兴祥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都依照此论;二是以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代表,将下限定为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三是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认为下限是1921年中共一大;四是认为下限到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建立,黄修荣著《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和刘宋斌、姚金果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都持此观点;五是提出下限应该延伸到1925年中共四大,认为“中共四大确定‘群众性党’的建设目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方式新思路,为迎接崭新的国民革命做好了准备。到这时,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真正完成了建党的任务”。
(二)关于中共创建的背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背景,多数学者从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社会基础等角度来进行论证,沿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的结论,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党是共产国际的产物”,“中共是马列主义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产物”等。
近年来,学者研究的视角逐渐拓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很复杂的社会背景。有学者提出“中共的产生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和矛盾剧烈运动和冲撞的产物”;有学者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诸多层面为中共创建提供的历史缘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有学者从国内政治环境、经济状况、文化背景和国际环境等方面进行论述;还有学者从政治学角度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政治背景、条件以及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的影响。
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不少学者注意到辛亥革命与中共创建之间的联系。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运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讲述了历史是如何从辛亥革命走到五四运动再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邵维正《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认为辛亥革命是近代爆发的多次救亡图存斗争中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政治上、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重要准备。宋键《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刘宋斌《论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推动作用》等,认为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营造了条件。这个论题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甚至可以考虑再向前追溯到甲午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因为中共早期人物大多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研究他们青少年时期的社会环境及对他们的影响,对于深化中共创建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首先在上海成立,1921年中共一大又在上海召开,说明中共建立与近代上海有着密切关系。唐培吉《建党时期值得研讨的几个问题》、于龙生等《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摇篮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中共在上海建立的各种条件进行了探讨。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又尝试从社会史、城市史研究等视角,进一步探索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深厚历史底蕴。
(三)关于中共成立时间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新世纪以来,有学者跳出以中共一大召开即是成立时间的框架,提出了新的看法。曾长秋认为党的成立应从1920年上海党组织建立之时计算。韩国学者徐相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时间是1920年11月中旬。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11月,其依据有:一是中共建党时期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11月发布,并被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1921年5月出版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所介绍,且把中国的组织称作“中国共产党”;二是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7日创刊。李三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个历史过程。1920年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酝酿建党的开端,1920年6月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建立是组织上建党的开始,而1921年7月中共一大才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洪小夏的《中共诞生纪念日前推问题刍议》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并考察了这个过程的起点和终点,阐述了中共诞生纪念日的演变情况,并运用政党学原理比较国内外其他政党的相关做法,重点介绍中国国民党对“创党纪念日”的确定,认为可资借鉴,提出将中共诞辰纪念日前推至1920年,至于究竟在何日,可以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1920年初,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路上,二人讨论了组建共产党一事,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说的由来。长期以来,尽管缺乏第一手文献资料的证实,但此说基本上成为党史学界的“定论”。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这一说法的源头是高一涵的系列回忆,这些回忆不仅前后不一,且1919年年底到1920年年初这段时间,高一涵远在日本东京,无法现场参与这一过程。止戈详细考证了陈独秀离京抵沪的时间、李大钊在天津出席会议一事,对高一涵回忆的真实性也提出质疑。萧超然则从高一涵同李大钊的关系、当时的历史环境等方面,分析了高一涵前后回忆不一致的原因,肯定了高一涵的回忆。
(四)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基础性资料有,姜义华主编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主要选录了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最初在中国出版物上反映的资料;代表性论著有周子东、傅绍昌等编著的《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作用、地位及诸多革命人士所作的贡献;田子渝等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是系统研究1918年至1922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情况的一部力作。
毛泽东曾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开始传播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准确地说是在1919年春到1922年。冯元魁等《“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吴根梁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年表》、齐卫平《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都对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进行了梳理。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途径,学术界基本取得了共识,认为马克思主义从东(日本)、西(西欧,主要是法国)、北(苏俄)三个渠道来到中国。石川祯浩1992年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对此作了梳理和研究。他的专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和扩展,全面梳理了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到中国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两个附录《中国社会主义书籍解题》和《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基本厘清了五四时期日本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翻译成中文的情况。都培炎《马克思主义从日本传入上海的逻辑轨迹》从宏观层面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从日本传入上海的历史轨迹和逻辑特征,认为这一过程有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与日本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有直接关联。
关于建党前后三次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以往研究普遍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驳倒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出现了一些新看法,尤以《〈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节录》中的观点为代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绳认为:“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派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陈文桂《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王文滋《胡绳关于早期社会主义论战的再评价》,都对胡绳关于早期社会主义论战的见解进行了介绍和诠释,认为“梁启超、张东荪反对当时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是反动的,因为资本主义在当时是进步事物”,陈独秀、李达等尽管“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但是他们在论战中也有弱点”,“实际上并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驳倒梁、张的意见”。至于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以往研究多认为无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障碍。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关注到无政府主义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影响,如简明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无政府主义》。陈桂香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与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考察了“互助论”、无政府主义在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邬国义的《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从<西行漫记>的一处误译谈起》,考察了毛泽东早年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以及毛泽东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五)关于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是共产党早期组织资料的集大成者。陈绍康编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迄今关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为详细的研究成果和资料集。另有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编、1980年内部出版的《湖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等编、1981年内部出版的《“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等。这些专题资料汇编为研究共产党早期组织打下了基础。
关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专题研讨活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较少。2000年,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6省市党史研究室在上海联合召开“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学术研讨会,重点围绕党的早期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主题进行探讨,既有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研究,又有对组织主要成员的研究。在对人物的研究中,既有对以往研究较多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人的研究,也有对以往关注较少的如王乐平、王翔千等人的研究;对创建时期的进步团体,如新民学会、文化书社的历史作用及其与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关系也有涉及。2010年,上海召开“纪念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围绕上海、北京等地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的背景、时间、过程、特点、历史地位,与上海发起组有关的人物,以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关于“共产主义小组”这一沿用时间最长的称呼,改革开放之初即有争论。有学者认为,将中共一大前建立的共产党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不准确的,是沿用了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称谓。“共产主义小组”来自于俄国,是列宁创建俄共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中共一大前各地建立的共产党组织,是具有政党性质的,并且从一开始就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称呼,而是称为“共产党”或“共产党支部”等。这一观点在学界很快得到共识。1996年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采用了这一观点。在2002年出版的修订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使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来统称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共产党组织。
关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上海学术界根据《俞秀松日记》,提出“社会共产党”是最早的用名。关于上海发起组的筹建时间,研究者基本认同发起组的筹建有一个过程,从1920年年中开始,开过多次会议,但具体到什么时间标志着成立,任武雄《中共创建史上两个问题的探索》认为是1920年5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史》则根据俞秀松日记的记载,辅之以施存统、陈公培的回忆,认为成立时间为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则采用1920年8月成立的说法。
与上海发起组有关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革命局”或“上海革命委员会”、“社会主义研究社”、“社会主义者同盟”等团体的性质问题,任武雄在《中共创建史上若干问题的探索》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应是社会主义研究社,是中共发起组的出版机构,同时也是早期研究、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关于上海革命局,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认为,上海“革命局”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金立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则否定上海“革命局”和中共上海发起组之间的等同关系,认为上海“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至于社会主义者同盟,任武雄《对“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探索》认为,这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和黄凌霜、梁冰弦、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在柏烈伟的斡旋下,为谋求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而成立的联合战线性质的组织。沈海波《试论社会主义者同盟》提出,社会主义者同盟是由吴廷康促成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相联合的产物,成立于1920年10月以后。
关于中共一大前的党员人数,有53人、57人、59人三种说法。张小红对这几种说法的原始出处进行了梳理,认为三种说法都值得商榷,至少53人说是不准确的。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等合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对此论题也进行了细致梳理,提出了58人说。中共一大主持人张国焘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课的提纲中,明确说是57人。
(六)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研究
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共的创建有着密切关系。目前,研究这一论题的专题著作还未见到。但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著作有:向青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杨云若和杨奎松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翟作君编著《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孙武霞等编《指令与自主:共产国际·苏联·中国革命》、翟作君主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荟萃》等,都把中共创建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为专题来论述。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境内华人曾组织起来,加入到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活动中,还组建了共产党组织。李玉贞《十月革命前后的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介绍了中华旅俄联合会、旅俄华工联合会以及俄国共产华员局三个组织及其活动情况。薛衔天、李玉贞的《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探讨了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旅俄华人中开展的大量工作,以及与建党问题相联系的对华革命策略方面的问题。薛衔天《关于旅俄华工联合会机关报<大同报>》介绍了旅俄华工组织在苏俄创办的宣传共产主义的中文报刊。
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针对苏俄、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早期机构的研究有了显著进展。如李玉贞《与中共建立有关的俄共(布)、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对苏俄和共产国际早期派遣使者到中国的官方机构———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进行了系统梳理。韩国学者金秀英《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组织集中化和国际主义因素之消亡》详细分析了远东书记处的诞生及其成为东亚共产主义运动支配力量的形成过程。俄国学者索特尼科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利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开展的早期阶段的工作进行了探究。
关于苏俄、共产国际派遣来华的人员及其活动的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吴廷康、马林等人的关注较多,如《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马林传》,但是对其他来华工作的苏俄密使研究较少。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的研究进展较大。其中,李玉贞和旅英学者李丹阳、刘建一及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等人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他们根据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共产国际档案、英国档案、日本外务省档案以及各种原始报刊等资料,挖掘出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红色俄侨和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活动情况。李丹阳《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从联络东西方革命者、传播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协助创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四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李泽洛维奇在中国开展的共产主义活动。李丹阳、刘建一《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悲剧:斯托帕尼在上海》,介绍了斯托帕尼从1919年冬至1921年3月27日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在《〈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一文中,他们又考察了《上海俄文生活报》的创办过程、基本内容、报社功能、人员组成和所起作用等,认为报社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而特殊的作用。李丹阳《肩负使命从俄国来华的一战战俘》考察了一战战俘在华进行的革命活动。李玉贞《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苏俄密使》,对布尔特曼、M·波波夫、阿加廖夫、波塔波夫、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吴廷康、斯内夫利特、尼克尔斯基、弗洛姆贝格等苏俄密使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梳理。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也用一个章节考察了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吴廷康等来华使者的活动以及苏俄、共产国际远东对华工作机构。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系,国外学者往往强调中国共产党是苏俄移植的产物。国内学者则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国际的帮助只是外因。翟作君《浅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作用》就认为,应当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但从本质上说,共产国际的帮助毕竟只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外部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趋向理性和客观,如肖甡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外因和内因是互为一体的,缺一不可,并且内外因作用的大小无法量化,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要从实际出发,深入探讨。
(七)中共创建时期会议研究
1. 中共一大研究
中共一大研究是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重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大量详实资料整理出版的基础上,学界对中共一大开幕日期、代表人数、代表资格、会议日程、会议内容、会议中的争论、30日发生的巡捕查房事件、闭幕日期等细微的议题都进行了研究,部分重要议题还形成了有代表性的结论。
关于中共一大的发起筹备,沈海波《再论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认为中共一大是自行筹备召开的,既不是马林的建议,也不是尼克尔斯基的建议。
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邵维正《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根据史实论证一大开幕时间应为1921年7月23日,而不是传统认为的7月1日。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公认,并成为权威表述。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多数学者认可13人说。解光一《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新质疑》认为中共一大代表人数应不拘泥于“12人说”和“13人说”,提出“南京和徐州在1920至1921年间,均有党的组织,并且在‘一大’召开前夕,接到了出席‘一大’的通知,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代表人数是徐州和南京各一名”。
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生平活动、形象及其对于中共一大的作用为研究者所熟悉,但另一位代表尼克尔斯基的情况却了解不多,其形象更是“历史空白”。2007年9月27日,经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和蒙古国历史研究所所长朝伦·达西达瓦的共同努力,尼克尔斯基的照片终于在俄罗斯鄂木斯克州专业档案馆里被找到,并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陈列出来,填补了空白。《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公布了尼克尔斯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2张头像和一张尼克尔斯基档案封面照片。该书刊载的张小红《尼克尔斯基照片重现记》、阿列克赛·布亚科夫《在寻找照片中已知晓的和还不知晓的事情》、朝伦·达西达瓦的《简述尼克尔斯基及其照片寻找过程》,分别介绍了照片寻找和发现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关于中共一大会议的会场,目前学术界肯定了主会场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城、李汉俊寓所,最后一次会场在嘉兴南湖游船上。陆米强《中共“一大”开幕式在博文女校举行的考证》认为博文女校举行了中共一大开幕式,因此是中共一大早期会场。中共一大为何会选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熊月之《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从城市社会史的视角进行了解读。
关于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有“7月31日说”、“8月1日说”、“8月2日说”、“8月3日说”、“8月5日说”等,至今尚未有权威的结论。目前比较严谨的论著,多用“最后一天”、“最后一次会议”来表述。
关于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会场突然被巡捕搜查的原因,任武雄《党的“一大”会址被搜查之谜》认为是因为马林的行踪早已暴露。朱华《巡捕闯入“一大”会场新说》认为是程子卿弄错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于偶然中发现中共一大会场的。关于这一晚开会时闯入的密探,鸡鸣(吴基民)和叶永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披露:据曾任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薛耕莘回忆,这位密探就是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程子卿是怎么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人们又是何时认定程子卿就是闯入会场的密探?程子卿究竟是位什么样的人,其人生结局如何?2011年有三位曾与薛耕莘有过接触或采访、听其讲述过这段经历的学者撰文,从不同的侧重点讲述了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前后因缘以及程子卿的人生经历。许洪新《中共一大会议中的突发事件》侧重推断30日晚发生突发事件的缘由。苏智良《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之考证》侧重于介绍程子卿与黄金荣的关系及其人生历程。吴基民《中共一大会议一段史实存疑》强调这一晚法租界的巡捕关注的目光是放在马林身上的;他们翻箱倒柜希望找到的是武器和炸弹,而不是针对准备成立共产党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
关于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以往回忆资料中都记载: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租船开会的事,是王会悟的主意,也是由她去操办的。孔海珠《谁是嘉兴南湖租船人》,对有关历史细节进行了补充,披露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是由作者的父亲孔另境出力联系的,当时他正在嘉兴二中读书。20世纪60年代初,修复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开会租用过的游船时,孔另境曾参与其事。
关于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央机关,吴贵芳《中共“一大”后的临时中央局机关和中共“二大”会址》认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选举成立的中央机关是临时中央局。王健英《中共一大后中央机关部门的建立》剖析了关于中央机关部门成立的几种观点,认为一大选出三人组成的应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2. 中共二大研究
学界关于中共二大的资料搜集整理,最早见于时光等选编《“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关于中共二大的第一部专题资料汇编,系统收录了中共二大通过的文件、决议案和二大前后相关的中央文件、共产国际文件、回忆录等文献资料,为学者集中查找中共二大的资料提供了便利。
学界对中共二大的研究集中在纪念会议召开的80周年、85周年、90周年前后。2002年、2007年、2012年,上海都召开了中共二大学术研讨会。学者围绕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中共二大的历史地位、中共二大召开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共二大史实考证、共产国际与中共二大的关系、中共二大相关人物及工农妇青运动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推动了学界对于中共二大的研究。
关于中共二大召开的日期,根据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国内党史界都采用“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说。石川祯浩根据中共二大宣言在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第1版中被第一次公开时的一些细节,认为中共二大的会期是5月还是7月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有关中共二大的考证论文很少,远远比不上中共一大的考证论文。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就大会相关文献的产生和流传过程、大会会期会址的定论是如何确立的、大会的代表名单变化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对二大宣言没有在大会前后公布而在1926年公布时出现日期偏差的问题进行了考证,推测其原因在于二大宣言从起草到完成,其间经过二大,时间跨了好几个月;关于二大的代表是谁,作者认为“现实是,无论我们如何探讨,只能说,出席大会的代表好像有7人左右,其中似乎肯定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达等,因为他们曾回顾自己参加大会的情况”。
3. 中共三大研究
学界关于中共三大的资料整理,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2006年,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修复开放。2003年、2006年、2013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多家单位联合召开了纪念中共三大的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中共“三大”研究》《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三大是一次争论激烈的大会,但大会究竟争论什么问题,这些争论最后怎样解决,以及会议的代表人数、大会开始时间等基本问题,以往多凭借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进行研究,而这些回忆又存在很多不一致之处。2000以来,一些学者根据共产国际解密档案,对此进行了全新的考证和研究,澄清了不少问题。金立人对代表人数、大会开始时间、中央迁址及三大在广州召开的原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问题、大会争论的问题、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利用”问题、如何结束分歧问题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如认为三大的中共代表数是40人,加上共产国际代表1人,出席三大的人数共计41人;代表大会的开始时间是192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从上海正式迁到广州是在1923年4月,迁址的原因是形势严峻;档案材料中并未发现陈独秀提过“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更没有将这句话作为口号,这一口号是对马林观点的概括,等等。
(八)社会主义青年团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研究的推动主要体现在资料的挖掘、整理、发表和史实的梳理上。1983年,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年)》,对广东早期党团资料进行了整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内部出版)收录了详细梳理上海、北京、广州、武昌、天津、江西、福建、唐山、杭州、南京、旅欧等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及其活动情况的18篇论文。1982年至1983年,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1—3集收录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关文献、报刊资料、团早期领导人的信函以及蔡畅、陈望道、柯庆施、李达、刘仁静等中共早期人物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情况的资料。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红旗飘飘》编辑部编《红旗飘飘》第31辑《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七十周年专辑》,是建团70周年时联合编辑的关于早期团员的资料集。专辑收录了一批早期党团员的家属、亲人、战友写的回忆录,以及熟悉老团员生平事迹的专家、作家为他们写的传记和故事;还收录了俞秀松烈士书信(19封)、王一飞烈士给妻子陆缀雯的信(36封)等历史资料。
1991年,任武雄撰写的《一篇重要报告的作者考———兼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成立时间》考证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应出自俞秀松之手,且由俞在大会上作该《报告》。并指出根据这一报告,可判定团的临时中央在1921年4月成立。
由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外名义是外国语学社,所以上海外国语学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研究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叶累等《外国语学社》、陈绍康《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创建及其影响》、申培仁《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对外国语学社的建立、特点及其在当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介绍和总结。沈海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解散的问题———兼论外国语学社结束的时间》指出,外国语学社结束时间应在1921年“五一”前后。陈绍康等《略论外国语学社几个特点与人才的作用》论述了外国语学社创立的社会背景,以及工作与活动的开创性、多样性等特点。
2004年,《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发布了4篇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中共早期历史的当事者关于青年团的回忆,包括《1954年3月包惠僧回忆早期青年团在上海渔阳里6号活动的情况》《1955年许之桢回忆早期青年团在上海渔阳里6号活动及原址布置情况》《1961年1月钟复光来信答复施复亮回忆早期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活动情况》《1966年4月华林回忆早期青年团在上海活动情况及团员青年赴俄国留学经过》,丰富了青年团的研究资料。
2010年召开的“纪念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纪念外国语学社创办90周年”座谈会,推动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历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刘雪芹《中共建党初期党团关系研究》、闵小益《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等。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何丹丹的硕士论文《建党初期上海党团关系研究(1921—1923)》,从党、团组织的基本概况、党团关系的主要内容、党团关系的特点、党团关系的制约因素及解决措施四个方面入手,对建党初期上海党团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起草者,以往研究多认为是瞿秋白、张太雷和青年国际代表达林,主要根据是达林的《中国回忆录》。李永春、暴宏博《蔡和森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考》就此进行了考证,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前后,瞿秋白正在莫斯科养病,并未回国,刚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参加了筹备青年团一大组织处,负责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在广州青年团筹备会上继续负责起草团纲。
2013年下半年,广州市团市委、广州青运史研究室组织人员到俄罗斯档案馆找到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时期的一大批珍贵档案资料,有:(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1次代表大会前的文件》,内容涵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团章、决议、会议记录、工作计划、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机构,还有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资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资料等,团一大的筹备及召开,团二大召开之前诸如筹备过程中关于团的名称、各地团组织的建立、各地代表的选送、名额等情况;(2)各地团组织的报告,记载了团酝酿时期的情况,如《保定社会主义团组织报告育德中学青年团组织审查委员会》《香港青年社章程》等;(3)《1920年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报道》(英文);(4)《1920年张国焘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纪录》(俄文手迹)。目前仅《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刊载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及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记录(1922年5月—1923年8月)》,而这批青年团史料价值斐然,期待能够早日被整理出版公布。
(九)中共早期人物研究
关于中共创建时期的人物研究,在各专题研究中是最活跃的,研究成果也最丰富。20世纪,学界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向警予等建党时期主要人物的研究、关注较多,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仅考证人物的活动、笔名化名等,而且对各自历史地位的评价更为客观;对于这些人物思想的研究,也从最初研究思想发展历程、政治思想等扩展到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中西文化观、伦理思想、妇女解放思想、法律思想、留学观等方向。如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被贬低甚至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得到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就明确提出:“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除了对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时期主要人物的研究外,对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后来脱党、有的甚至成为“汉奸”的人物的研究也不再有禁忌,至于杨匏安、黄负生、安幸生、黄日葵、张若名等研究非常薄弱的人物,也被逐步重视起来。如李坚《五四前后的杨匏安》,对杨匏安在五四前后的活动及思想进行了仔细考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黄负生的女儿黄铁也对其父的革命活动和思想进行了研究。吴海勇《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季翻译经历考述》《李季在创党时期的思想行动轨迹》,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季在1919年到1921年的翻译经历进行了详细梳理。近年来召开的一些专题性学术研讨活动,对过去中共早期人物中研究比较薄弱的人物进行了专题研讨,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2007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组织召开“纪念李汉俊烈士牺牲80周年座谈会”,围绕李汉俊的生平事迹、思想、贡献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学术探讨。2008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召开“纪念王尽美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2009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党史学会、卢湾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多家单位协同举办“纪念俞秀松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还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主编《秀柏苍松———俞秀松研究文集》。2009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单位组织召开“纪念袁振英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2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刘仁静与中共创建学术研讨会”;广州举办“金家凤研究座谈会”;中国现代史学会、四川音乐学院和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2013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纪念陈潭秋牺牲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江苏举办“金家凤在中共创建时期的历史作用暨诞辰110周年座谈会”。2014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主办“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研究学术研讨会”,等等。
三、小结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历程不难发现,中共创建史研究发展较快的时期,往往是党史工作者挖掘、整理、刊布史料最勤勉的时期。中共创建史研究若想取得更深入的进展,除了向其他学科学习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外,最重要的还是尽可能去挖掘整理新的档案史料。本文作者之一张玉菡近年来参与编辑《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李汉俊文集》以及《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对于挖掘新史料的意义深有感触。她撰写的《包惠僧与武汉五四运动》105 一文就是建立在新挖掘的包惠僧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该论题虽然很小,但也算是填补了包惠僧与五四运动关系的研究空白。同时,重视对已有史料的研究,也是推进中共创建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方面。有些史料看似习以为常,但以不同视角来看待,以不同方法来研究,也会有新发现。甚至同一个史料在不同历史时期来研究,也会有不同理解。相信在有志者共同努力下,中共创建史研究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