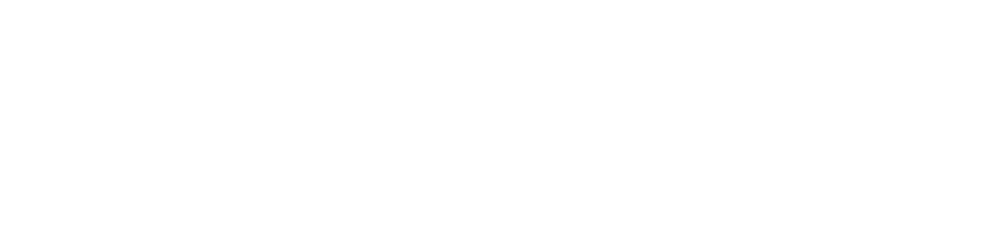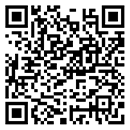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中共一大在中共创建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无可置疑的。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一大研究一直是党史工作者十分关注的课题。进入新世纪,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全国各地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共创建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史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美〕舒衡哲编《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吴少京主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等。这期间刊出的新发现的重要资料有《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立的文件》9件(2001年《百年潮》第12期)、《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2002年《百年潮》第2期)。著作方面最有影响的是2002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这是一本涉及中共创立的权威著作。此外曹仲彬著《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宋斌、姚金果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马连儒著《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日〕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工具类书籍有倪兴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十年来发表有关中共一大研究文章100多篇,召开过多次全国或地区性的一大学术研讨会,对中共一大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推动了一大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 关于一大的发起与筹备问题
对于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以往学术界根据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的回忆认为,马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所以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有关。还有学者提出尼科尔斯基 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 最近有学者否定了此说法,认为中共一大的发起者不可能是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是自行筹备召开的。虽然在名义上马林协助尼科尔斯基,完成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但在全局性的工作中,马林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另外从两人的经历来看,马林赴华时已经拥有在东方殖民地工作的丰富经验,这一点远非尼科尔斯基所能比。所以不难理解马林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共的早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尼科尔斯基来华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并没有因果关系。中共一大的召开不是马林的建议,更不是尼科尔斯基建议召开的。
(二)关于代表人数和代表资格问题
史学界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有争论,主要是12人说和13人说,以往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上,最近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一大会议又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1、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争论一直比较多,有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两种主要说法。正式代表说又分为三种:一是湖北代表说,这种说法主要见之一大代表张国焘的回忆。二是广东代表说,在一大代表中,周佛海、陈潭秋、董必武及包惠僧本人都持这一说法,在学术界支持这一说法的也比较多。 三是陈独秀指定代表说。 非正式代表说则有两种说法:一是串门子说,出自一大代表刘仁静;二是观察员说,此说最早出自日本学者小野信尔的《图说中国历史》一书(1977年版),在中国学者中也有持该说者。 近十年中有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观点比较一致,即包惠僧是广东代表。 此外还出现了新的说法,即包惠僧是临时中央和陈独秀之间的联络员。 作者认为包惠僧代表资格争议的原因是没有搞清他的身份,包惠僧不是代表,是陈独秀派往临时中央和向大会组织者说明情况的使者。研究者通过分析广东党组织推举一大代表的过程,又根据包惠僧5月由上海到广州、7月从广州回上海、一大后又回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指出:“他有不是代表而有可能参加大会比一般党员较特殊的身份,是陈独秀派向临时中央和大会组织者汇报说明情况的使者”,正是这种特殊的使者身份使其能够接近李达等大会组织者和大会代表,能够进入会议的秘密地点博文女校,能够自始至终参加大会且被大会委以至关重要的保卫工作。李达作为大会的召集者、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最清楚包惠僧的身份,最应该知晓内情,其回答应具有权威性,他从不承认包惠僧的代表资格。而其他代表则对此看法不一:有的(如毛泽东、刘仁静、董必武)认为,既然他不是各地党组织选出的代表,所以不算正式代表,即使参加了也是列席;有的(如张国焘、陈潭秋)认为,既然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在一大讨论中积极发言并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又考虑到他原是湖北党组织创始人和负责人,且1921年1月就参加临时中央,就应该算代表。至于属于何地的代表,有人认为他来自广东,自然属于广东代表;有人认为他原是武汉的党组织负责人,把他归于湖北代表(如张国焘);有人认为他是陈独秀派来的,所以是陈独秀的代表。此事是因参加者理解不同才有不同的提法,大会对此并没有统一认识。
2、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一大
何叔衡是中共湖南早期组织选出的中共一大代表,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一大,有一定探讨余地。提出这一疑问的依据来自张国焘。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学者认同这一说法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说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反响,在一些有关中共一大研究综述的文章中甚至都没有提及。进入新世纪后,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证。 作者根据陈公博1924年回忆、党的六大上绘制的一大代表名单、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复信、《毛泽东自述》、其他一大代表的回忆、《谢觉哉日记》等十几个方面的材料进行分析后肯定地说: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
(三)关于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
由于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已经基本确定,长期以来一大的闭幕日期成为中共一大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也比较多。关于这个问题,2001年以前大体上有四种观点:
一是7月31日说。 主要依据董必武、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多位一大代表的回忆。
二是8月1日说。 主要依据董必武和张国焘的回忆。
三是8月2日说。 主要依据王会悟的回忆。王会悟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是大部分代表在回忆中都提到南湖会址的具体安排是她一手承办的。因此她关于一大闭幕时间的回忆,应该比较可信。
四是8月5日说。主要依据前苏联档案《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和陈公博的回忆。一些学者认为“8月5日闭幕一说更有说服力” 。
近十年中,学者们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7月31日说已经被基本放弃,但对8月1日说 ,8月2日说 ,8月5日说 ,则依据新的史料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同时还有学者提出了8月3日这一新说法。 作者首先否认了8月5日闭幕说,原因是: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中央局成员回上海后一定会召开一个中央局会议具体部署中央工作,会后也肯定会向马林等告知一大会议和中央局会议情况,或者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直接参加了中央局会议。刊登于《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写道:“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斯穆尔基斯的一手材料来自尼克尔斯基,而尼克尔斯基或斯穆尔基斯可能将一大毕会时间和选出的中央局成员在上海开会的时间混在一起了,这可能是8月5日闭幕说法的由来。而8月3日闭幕的理由是:第一,根据《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和《申报》关于该案的报道可确定陈公博携新婚妻子去杭州是7月31日,回上海应是8月3日或4日,考虑陈公博回上海后与周佛海等联系不便等原因,周佛海找上他尚需时间,大会应该于8月2日或3日结束。又根据王会悟“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的回忆可分析出:是“两天以后”的2日决定续会(“两天以后”是指8月2日),经部分代表提议决定8月3日到嘉兴南湖续会,于是通知所有在上海的代表,并派王会悟到车站了解情况。第二,考虑8月5日回上海开中央局会议,8月3日闭幕更合理:若8月1日或2日一大已闭幕间隔时间太长。第三,8月3日闭幕,更符合“隔了4天”说(31日至3日)。
(四)关于“南陈北李”未出席一大的原因
在中共创建过程中,被称为“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均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两位主要创始人却同时缺席一大,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一直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对于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以往学术界主要认为是由于公务繁忙无法出席大会 ,依据是陈潭秋和包惠僧的回忆。而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种说法:1、为了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年会 ;2、因为校务繁忙 ;3、领导北京教职员“索薪斗争” ;4、因为受伤住院。 总的来看陈独秀、李大钊两人都是因为公务繁忙,所以没能出席中共一大。
最近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包办一大有意见 ,公务繁忙只是他拒绝出席一大的说辞。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是北京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在选举一大代表时,没有推选他。 还有学者认为,透过“公务繁忙”的表象,“南陈北李”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一大会议不重视。 因为在他们两人看来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便成立了,参加不参加一大意义并不大。
(五)一大会场突被巡捕搜查的原因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正式开幕,之后几天的会议一切正常。但是7月30日晚,法租界巡捕房派出十多个荷枪实弹的武装警探,突然包围会场进行搜查,不久撤走,全体代表安然无恙。这曾是一个疑案。在一大代表的有关回忆中,说到被搜查原因的有四人。张国焘说:“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所以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在马林与尼可罗夫 参加时下手。” 陈潭秋的回忆与张国焘的说法相近,他说:“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 李达回忆说:一大会场被搜查“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巡捕听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 董必武说:“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 以上的回忆都只是他们自己的推测,没有什么根据。
有学者根据警察局有关档案认为一大会址被搜查是因为马林的行踪早已暴露。 后来日本学者根据荷兰外交部几份档案再次肯定了这一说法。 不过最近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否定了这一传统说法,认为这是巡捕房华人侦探程子卿偶然中发现一大会场的。 当时程子卿向位于一大会场隔壁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无意中发现了一大会场。作者以前认为程子卿之所以能发现会场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走错了门,二是因听到106号有外国人说话而引起了疑心,于是强行闯入。但是后来根据材料发现,程子卿是因为弄错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而误入会场。也正因为如此,当程子卿发现一大会场时,一时也没了办法,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而这来回之间的时间,就成了一大代表们脱身的机会。
(六)关于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对于这一选举产生的机构情况,长期以来的说法认为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面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但是有学者认为,称一大“选出”中央局,并无原始文献依据,中共一大选出的三人应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与张国焘、李达会合后,组成党中央常设机关——中央局。由于执委会委员只有三人,因此同时兼中央局委员。实际上是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中央局”。其主要根据是:其一,一大党纲与决议的规定。其二,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三,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通信称,代表大会在结束时选出了由四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总部主任就是其中之一。 其四,一大代表张国焘、董必武等人的回忆。其五,早期文献史料的讲法,如蔡和森1926年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邓中夏1930年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
(七)一大会议文献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是中共一大通过的两个正式文件,不过它们只有俄文本和英文本,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其中文原件。但是这两个文件对一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研究更是如此,因为纲领是一个政党的旗帜。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所缺失的第十一条内容及缺失原因,曾有人进行过初步考证和研究。关于缺失的原因有这么几种说法:1、遗漏说。 2、技术错误说。 3、删除说。 关于其可能的内容也有几种说法:1、有关党的宣传工作。2、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3、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4、有关党的组织原则,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
近十年来学者们对一大党纲的文本内容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将一大《纲领》与《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俄共党纲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认为:“‘一大’党纲的理论渊源于《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以及俄共党纲,因为‘一大’党纲中的‘党的名称’、‘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入党条件’与上述文件及纲领中的规定有很大相似之处。” 而日本学者通过考证比较后,指出一大的文件是以美国统一共产党的党纲作蓝本的,“章程的蓝本是《共产党》月刊第2期翻译发表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决议也分明参考了刊登在同一期《共产党》月刊的《美国共产党宣言》”。
还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文本属性进行了研究,通过对纲领的体例、内容等方面的研究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性质应该是章程,即党章,所以,应该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简称“一大党章”或“一大章程”,这样,既准确地揭示了文件的性质,也合于长期以来党内生活所形成的习惯。
同时有研究者重新解释了中共一大没有采纳列宁殖民地革命思想的原因:“第一,在中共‘一大’时共产国际与中共在组织上尚未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还有制定政策的独立性,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来舍取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在中共‘一大’时中国共产党人还缺乏全面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限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在组织方面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水平,中共‘一大’未能采纳列宁的殖民地革命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是否是中共一大正式文件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这两份被我们长期当作正式文件使用的文献中文本,是译自1957年苏联归还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俄文本。2006年春,作者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看到了这两份文件的俄文本。它们分别是一个名为“中国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文件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作者经过对它们以及该文献英文本的来源和内容的分析,同时根据对一大议程的史料梳理,认为,由于在一大会议中存在许多争议的地方,所以一大未曾通过正式的纲领和决议,我们现在看到的文件很可能仅仅是一个草案,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汇报材料。
(八)关于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
在中共一大的15位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他们分别是俄国人、共产国际使者尼克尔斯基和荷兰人、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而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正式代表马林。
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强调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依据主要来自一大代表事后的追忆。包惠僧回忆道:“中共‘一大’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他到上海之后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商定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会议” 。近年有学者撰文认为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可能并不像以往人们认为的那么大:“他到上海后,配合尼克尔斯基工作,参与了‘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部分地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会议,并及时识破了闯入会议室的租界暗探的身份,使这次会议得以继续异地举行。会议期间,马林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主要观点并未被多数代表接受。”
而对参加中共一大的另外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在一大期间的作用如何,研究者一直不是很清楚。包惠僧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很多党史专著、教科书干脆不提尼克尔斯基这个人,即便提及也只是承袭包惠僧或张国焘的说法,而关于他的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
不仅我国学界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知之不详,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也曾经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是缺少此人的档案材料。近年来,俄罗斯和蒙古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查到了尼克尔斯基的档案,将他的身份搞清楚了。原来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去的,任务主要有这么几项:1、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2、担负职工国际(更确切地说,是在赤塔设有分会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职责;3、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华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 另外还发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也填补了长期以来所有历史书籍和陈列展览中,中共一大15位参加者照片不全的缺憾。
综上所述,在过去十年里,中共一大研究取得不少成绩。总的来看取得的成果还不是太多,主要表现在近十年以来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数量相比前十年要少,提出的新观点不多,很多有争议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原因首先是人才缺乏。很多原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专家学者转向去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人才青黄不接。其次是资料匮乏。由于中共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后来又长期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中,关于中共一大的原始资料很少保存下来。过去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大都是在30年代中期以后写的,史实尚欠准确详尽,说法也极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所以在中共一大研究中产生了很多有争议的问题,要统一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掘和深入研究。
今后该方面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努力培养一批有志于中共创建史研究的青年人才。第二、进一步开放历史档案、发掘史料。如上世纪90年代公布了一大批共产国际档案,对中共创建史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第三,在继续进行微观研究的同时,加强宏观研究,特别是对中共一大召开的历史条件、功绩和局限性以及历史影响等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已经出版的所有有关一大的专著,基本都反映中国共产党整个建党的历史,只是把中共一大作为一章或一编来论述,因此,严格来说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中共一大史》,这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应该尽快出版一部系统的高水平的《中共一大史》。第四,应该拓宽研究领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中共一大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还要通过比较研究,如把中共一大与中共二大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立等等加以比较,使研究进一步深化。